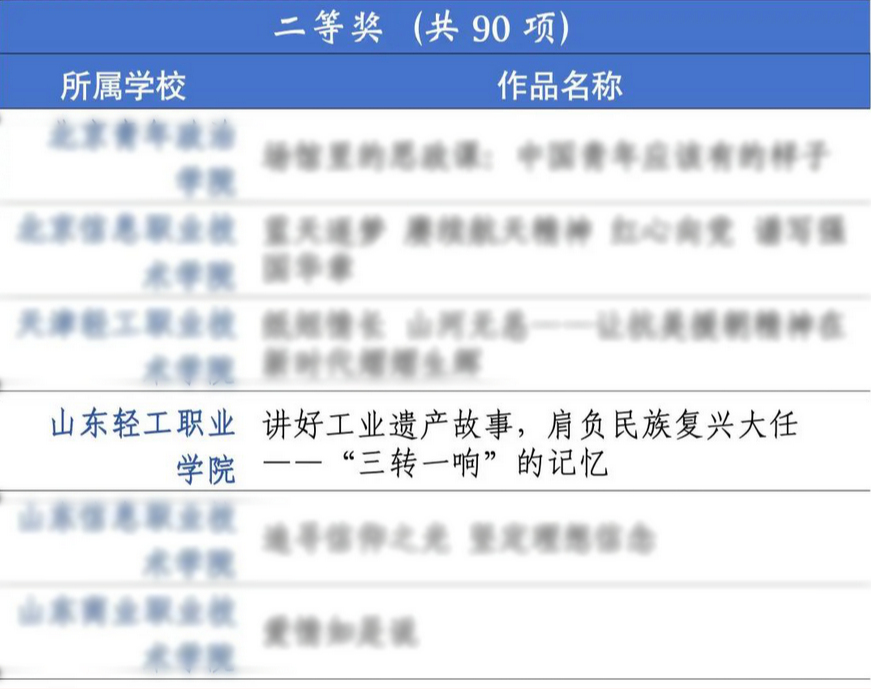上高二时我第一次出远门,说是远门,其实也不远,也就是到离家约170公里的绍兴柯桥。如果是现在,这点距离驱车两个小时就能到达,但是在没有高速公里的二十多年前,这170公里路硬生生走了近六个小时:因为我们家到柯桥没有直达班车,必须到义乌转车——早上六点多从家里出发,九点到义乌,到达柯桥时已经接近下午一点。
当然,这次出行最大的印象并不是遥远、颠簸的路途,而是在绍兴柯桥吃到的食物。到现在为止,我依然认为1994在柯桥吃到的青椒肉丝是我这辈子吃到的第一个美食。你没看错,对,就是青椒肉丝。现在来看,这道菜实在是再简单不过,就是切丝的青椒和肉丝。但是在那时,却是把我和我爸给震惊了:青椒还有这种做法?

因为在我们家,青椒都是切片的!猪肉和青椒在一起,也都是成片状,而不是切成丝。尽管我们那是青椒生产基地——几乎每家每户都种植青椒且每年会有相当一部分青椒被贩运到大城市,但有趣的是,青椒的做法却异常简单,甚至可以用单调来形容,大家都是切片炒肉片或者是炒青椒。
尽管切丝比切片复杂了些,但这个难度并不足以成为一个技术壁垒而难倒所有人,那为什么我们那没有青椒切丝的做法?这个问题随着我年岁的增长慢慢遗忘了,直到在《舌尖上的中国2》在CCTV播出,看到那里有对中国各地美食的赞颂,甚至每一个乡村里都能遇见美食家。
乡村里真的有这么多美食吗?看到这么多人在媒体上的讨论,我突然想起来20年前在绍兴柯桥吃的青椒肉丝。为什么我们那里没有青椒肉丝?为什么我们那里的菜式如此简单甚至单调?家乡尽管有各种好食材,比如说我们那里是“中国香菇之乡”,有着全中国几乎最好的香菇,但是在任何一家农户或者乡镇的小馆子里,有关香菇的做法还是很简单,而且也不会让人觉得这是美味。

只有到了县城,香菇的做法才丰富起来,成为大家所钟爱的美食。香菇作为我们那里最拿得出手的食材,是县城各大饭馆里的主打产品,香菇有着各种各样的做法,油焖、青炒、油炸……从乡镇到县城,同属一个区域地理上也就只有十几公里的距离,为什么农村或者乡镇就没有县城这么丰富的做法?
现在想起来,其中的原因可能和当年我们那里只有青椒肉片并没有两样。首先,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在乡村里没有社会分工。尽管做菜吃饭是每天必须经历的事,但也就是个一个必须完成的动作而已——一个为了消除饥饿而必须完成的规定动作。在我印象中,一个镇也就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饭馆,绝大多数人都是在自己家里吃饭,极少有下馆子机会,在那个只能解决温饱问题的年代,谁有事没事下馆子?没有足够多的就餐人口,饭馆里的大师傅当然也就不会有激励去开发新鲜菜肴。
对于那些从未在饭馆里吃过饭菜的家庭主妇而言,尽管从小到大一直在炒菜做饭,但她们也只能是重复上一代的做法,她们从娘家里带来的炒菜手艺和婆家的手法并没有多大的区别,最多只是放盐加油的分量会有些许差别——而且这个差别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和饭菜的美味联系在一起,而是衡量一户人家慷概与否的标志。到现在我还记得到某亲戚家吃饭,他们家做的菜几乎看不见油荤,我以后就发誓,今后再也不到他家做客吃饭去了,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油盐是每家每户的重要生活资料,油荤确实是衡量一户人家是否慷慨的重要标准。
一般来说,在同样一个区域,食材种类并不会发生显著的变化,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数量多寡。对于家庭主妇而言,她所要做的事就是按照上一代传下来的做法依葫芦画瓢就可以。对于绝大多数老乡而言,一辈子鲜有在外下馆子的机会,当然没有办法评判自家婆娘做饭的水准,只知道油盐是否符合口味。
为什么城里的饭店会想出香菇的各种做法,而我们老乡的做法却那么简单?家庭主妇没有激励因素是一个重要原因。城里的饭馆会有各种激励去提高厨艺,因为越好吃的饭菜会吸引更多的客人,而客人增多会提升饭店利润,利润增加之后老板可以给厨师发放红包或者加薪水,这样厨师就有激励去寻找各种食材之间的搭配,为顾客奉献美食。
但是对于家庭主妇而言,专研厨艺的做法并不能够增加收入,而在很多时候新做法往往意味着耗费食材——为了获得一个好口味必须要做实验,而做实验则意味着要耗费食材。曾看到一个报道,说是1973年上海城隍庙为了让远道而来的西哈努克亲王吃到地道的鸡鸭血汤,要求一碗血汤中的鸡卵达到“三同”标准,即直径相同、色泽相同、形状相同,城隍庙的厨师足足杀了108只鸡才找到如此高标准的鸡卵。一个鸡鸭血汤要耗费108只鸡,不要说乡野村夫是闻所未闻,即便现在城里人听起来也是瞠目结舌。

也正是如此,耗费食材专研新菜在物质匮乏的乡下是不被赞赏的行为。谁家如果尝试新菜,必会被他家人制止。时代进化保留下来的家常菜做法必定是最能节约食材的。同时,家庭主妇除了做饭等家务之外,她还必须下地干活。每当她从田间地头回来之后,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做好饭菜,因此家常菜的做法还必须是尽可能节约时间,于是做菜的方式也就越简单越好。为什么家常菜里片多于丝、大块肉多于肉丁?这可能是一个重要原因。
城里的大厨师如果厨艺下降,就会有被辞退的风险,因为这意味着会带来客流下降而导致利润降低。但是对于家庭主妇而言,这样的风险并不存在。如果以现在饭馆的标准来衡量很多乡亲做的饭菜,有时候我会有难以下咽的感觉,但是做这些饭菜的家庭主妇并不会因此而下岗,原因可能是如前面说的乡下人很少有吃美食的机会;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不是她做,她的丈夫可能会做得更差。从小到大,没听到过一家子是因为饭菜做不好而日子过不下去的,却时常听到有人在抱怨谁家的媳妇嘴馋——现在回想起来,嘴馋实际上就是对美食怀有追求,可惜的是,乡下容不下这种追求。
当然,村里也会有一些“业余做饭的高手”,这些人往往是红白喜事时的大厨。如果稍加留意,你就会发现这些人往往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经常在外面跑。我爸就是我们村里“业余做饭的高手”,在我看来,他的厨艺也很一般,但为什么会被村里人这么器重,以至于每有红白喜事必请他掌勺?现在我觉得这可能和他的经历有关:17岁即入伍参军,到部队里呆了几年,在我们那小村子里也算是见多识广——比大多数乡亲多知道些饭菜的做法,因此每每担负起掌勺大任。但即便见识如我爸,也想不到有青椒肉丝这种做法——因为当时他入伍时没有这种做法。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不断加速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城镇建设速度加快,大量农民离开故土,奔向城市追求财富梦。近三十年来,随工迁徙的除了人,还有这样一种情愫也被带到了城市的各个角落——乡愁。
乡愁,作为一种现代化的情绪,让多少进城人又爱又恨。一面是落寞的故乡,一面是城市的财富吸引,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唯有逃离故乡,但随着客居的日子越来越长,回往进城路,对故乡就又多了份眷念。当初,城市给予进城农村人的是新奇,当新奇过后,农村召唤他们的是回归。小时候,一缕炊烟,故乡就弥漫在熟悉的香味里。进城后,就再难遇炊烟,难遇那小时候的味道。所以有时候离乡人会想到回归,回到故乡,回味那熟悉的故乡味道。虽然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做一方菜,但是随着人口的流动,地方味道也逐步被传递到城市的各个角落,成了许多新城市人乡愁的寄托。
总觉得节日也是一种乡愁,这些特定的时域节气总能唤醒记忆中的场景和味道,比如那些散落在城市角落里的地方小吃,总有种故乡的生活味道。笔者是湖南人,在太原的时候,每逢佳节总喜欢和几个老乡一起去一家湘粉馆。比起在城市大部分地方说一口浓厚的乡土话被当成一种忌讳,往往让人尴尬,甚至落荒而逃,在这家湘粉店,从老板到服务员都是一口家乡话,虽然是陌生人,但是熟悉的故乡话却能让人瞬间觉得受到了故乡人毫无保留的欢迎。湘粉师傅举手投足间,总让人有种家人的感觉。在香气浮现的湘粉店,有种在城市里遇见故乡的感觉。

不得不承认,在现代化的冲击下,故乡正在很多人的记忆里加速消失,“乡土中国”正在逐步褪去往昔的色彩。“安土重迁”也已不再是新一代进城人的所思所想。金字塔形的故乡族群结构不断延伸,越往下,族群越分散,族人在城镇化的进程中被冲散到城市的各个角落,各种小吃、美食也跟着他们穿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甚至成为了族群联系的纽带和场所。
乡味在城乡间循环,或者更准确地说,乡味随人从农村飘向城市,成为进城人的乡愁寄托。相比于那些自诩特色的大饭店,反而是制作场景更加相似的巷子里的小吃更具有故乡的生活气息。一碗牛肉粉、一碗刀削面、一个煎饼果子······
在城市中保留故乡的生活场景和生活方式,是对过往的尊重。而只要有过往,就会有乡愁,哪怕是从未离开过故乡的故乡人、哪怕是出生在城市里的城市人,看着生活中那些曾经熟悉的场景逐渐消逝,总会有种浓浓的情愫。在物质追求日渐丰富的时候,在日益挤压的城市空间内,追寻故乡的味道,或许就是我们身上保留的少有的人文情怀吧!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可是这又谈何容易。真正的“自然”一定是源于大山之中的。在外漂泊,难免会思考,就会想起故乡,想起的除了亲人,或许就是泥土气息里的“湘”味了:米耙粑、香肠、血饼、和渣、腊猪蹄、杀猪饭。在哈尔滨、广州、杭州、石家庄甚至更多的城市,虽然也吃过这些美食,但总吃不出小时候熟悉的味道。想起了《过年好》里的那句台词:“一个地方的水一个味,一个地方的材料不一个味”,总算真正理解到了这句话。

无论离家多远,在人们的脑海中,只有故乡的味道熟悉而顽固。它就像一个味觉定位系统,一头连着自己,另一头则永远牵绊着记忆深处的故乡。我的GPS则一头在我身上,一头,在西安……
洁白的面团早已醒好,光滑得如同一休的脑袋,在母亲的手中迅速地变成了扁平的条状,抹上油后,它们服服帖帖地堆在盘中。此时,白玉般的面被镀上了一层金光,犹如君王一般散发光芒。
再次醒发后,母亲从盘中拿出面条,原本僵硬的面条在油的滋润下变得柔软而有韧性,两手一拉,竟轻松地变为一条宽宽的玉带,“啪啪”的声音随着面条的起伏有规律地响起。等到声音停了,一根根面条出现在案板上。原本不过一指长、一寸宽的面条被拉成四指宽、一米长的面条,面条比刚才更加圆润,隐隐还能看出撞击案板时留下的木纹。
锅里的水已经起了白泡,“嗞——嗞——”一声比一声悠长。母亲从案板上揭起温润如玉的面条,下入翻江倒海的锅中,锅里的水立刻平静下来。又一次,锅里的水开始翻滚,母亲捞出了面条,那面条薄而不断。
面条盛入碗中,放上烫熟的青菜、胡萝卜、豆芽……最重要的是撒上火红的辣椒面和翠绿的葱碎。待锅中油烧得滚烫略有青烟时,将那热油泼入面中。“嗞啦——”一瞬间,辣椒面和小葱的香味被激发出来。热锅里再倒入香醋,又是一阵嗞啦作响,烧过的醋,没了酸涩,满是酸香。种种香味不经意间飘入鼻腔,原本沉寂的胃突然“咕噜噜”地叫起来,口中的唾液也不自觉地加快分泌。
晶莹剔透的面条上,如火的油泼辣子刺目的红,豆芽顶着大大的脑袋,全身换上了油亮的彩衣,青菜叶绿得发亮。夹一根面条,高高挑起送入口中,那味道惊艳着你的味蕾,督促着筷子不由自主地伸向碗中,再挑起一根又一根……
我在异乡虽也吃过油泼面,但总觉得差了些滋味,不地道。现在想来才知道,家乡的面永远比别处的面多了一种调料,那便是乡愁!